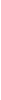她“嗷”了一声,张口要咬年素鸢的手。年素鸢冷笑一声,反手就是一耳光。
“简直像条疯狗似的。”一旁的嬷嬷抱怨道。
年素鸢一字一顿地说:“钮钴禄氏明椒,你可以发疯,可以忘了所有人,可以忘了你曾经做过什么,可是你忘不了弘历,对不对?”
她分明看见,明椒涣散的眼神微微一滞。
呵,果然。
她慢慢地说道:“你想不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?呵,他死得可真惨呢,直到去世前的最后一刻,还在埋怨你这个给他带来奇耻大辱的额娘……”
“你说谎!!!”明椒狠狠甩开了头,杂乱的长发遮住了眼。
哟,看来还挺清醒的嘛。
年素鸢幽幽地叹了口气:“看样子,你是故意装痴扮傻了?”
“哈——”明椒哑着嗓子说道:“你也活不了多久了!你——也活不了多久了!!!”
她疯狂地大笑,将疯妇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啧啧,怎么看,都像是在装疯……
“听着。”
年素鸢凑近了她,低声说道:“本宫会将你关在这里,拉上黑帘,塞上所有的缝隙,没有光、没有食水、没有人陪你说话……你最好祈祷自己是真疯,否则,你越清醒,就越是难过……”
“本宫不会将你活活饿死的。”
“在你崩溃之后,本宫会亲手喂你鸩酒,给皇上一个交代。”
“不过,谁知道鸩酒是在生前饮下的,还是死后灌下的呢……”
她无意中抬起头看了一眼,发现嬷嬷们眼里满是恐惧。
哈,这样的皇贵妃,简直就是魔鬼,对不对?
年素鸢恶意地解开了明椒的一颗盘扣,低声说道:“对了,本宫还要带走所有的蔽体之物,在屋角放两个炭火盆子。冻不死你,但绝对可以让你羞}耻难耐——想不想试一试?”
明椒张开了口。
年素鸢顺手将旁边的一团破布塞了进去。
她还得提防明椒咬舌自尽呢。
“方才本宫说的,你们都听到了?”
“奴婢等听到了……”
“照做!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记住什么是该说的,什么是不该说的,否则——”
“是,钮钴禄氏是娘娘赐了鸩酒,亲手送上路的!”
很好。
年素鸢站起身来,笑道:“本宫就在外头,你可别乱叫哟!”
明椒唔唔地叫着,眼里已经带了几分恐惧。
所有人都走了。
屋子里暗无天日。
地火龙和炭火盆子提供了足够的温度,不会让感觉到寒冷。
她的手脚都被牢牢地捆绑在了床的四角,赤|裸着身子,以极其……的姿态摆放着。
明椒的神志尚维持着一丝清醒,否则便不会对年素鸢的话产生如此大的反应。
但是,她开始恐惧。
她从未想过,黑暗与寂静是如此可怕的存在……
脚步声响了起来。
年素鸢的声音在她耳边回荡:“对了,本宫改主意了。本宫要绑住你的眼睛,然后开门——你应该晓得,外头有多少人,男人。”
明椒唔唔地叫着,身子微微颤抖。
年素鸢亲手将明椒的眼睛用黑布遮住,而后离开。
“看严实了,别让这屋子漏一丝光进去,否则本宫揭了你们的皮!”她压低了声音吩咐道。
嬷嬷们连连称是。
年素鸢命人端了把椅子来,坐在小黑屋外头,悠闲地磕着瓜子儿。
她已经可以想像,里头的明椒肯定恨不得自己是真疯……不过,如果她真的疯了,这个游戏也就没有意思了,对不对?
她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恶人,坏到了骨子里。
不过比起里面那位,还是欠了那么一点儿火候。
明椒很痛苦。
她恨不得自己立时死去。
她的精神并不是很好,时而清醒、时而糊涂。若是碰上她糊涂的时候,懵懵懂懂地就过去了;若是碰上她清醒的时候,简直就是极至的煎熬。
她隐约感觉到无数道目光在自己赤|裸的身体上游弋——虽然这根本不存在。
她什么也看不见、听不见,便开始想着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,譬如外头那个心狠手辣的女人或许会让人过来……对她……
不,这里是后宫……皇上不会让她这么做的……她会死的……她一定会死的……
真是……
极至的辱啊……
尤其是……
偶尔有几丝若有若无的风,吹过大开的双腿之间……
她恨自己没有真疯,没有真正的、彻头彻尾的发疯!
她宁可自己立时就疯了、死了,也好过像现在这样!!!
年素鸢用帕子捂着口,低咳几声,又顺手将帕子丢进了炭火盆子里。
一股铁锈的味道直冲喉头。
她已经听见了房里细微的呜咽声,还有身体扭动的声音。唔,明椒在试图挣脱绳索的束缚么?果然不是真疯啊……
年素鸢闭了闭眼,胸口愈发闷了。
明椒必须死在她前边。
必须!
明椒的精神终于崩溃了。
在一个极度封闭的空间里,完全的黑暗和安静,任何一点细微的声响都会被无限放大,脑中偶尔会闪过一些奇怪的画面。譬如,找她复仇的鬼婴……
她是被自己想像出来的世界给逼疯的。
然后,她终于挨不住了,在几次剧烈的颤抖与抽搐之后,晕了过去。
年素鸢捏着她的鼻子,直接灌了鸩酒。
然后,皇家玉牒上多了一个病死的熹常在。
——毕竟皇家的脸面,还是要顾及一些的,对不对?钮钴禄氏先前做的那些事儿,可真真成了宫闱秘史了……
年素鸢对自己亲手送明椒上路这件事感到非常满意。
而做完这一切之后,她终于病倒了。
据说,是感染了风寒。
第2页
46、染沉疴(三) ...
“这春寒料峭的,忽然就病了,也不是什么奇事……”
“该不会也跟皇后同一遭罢?……”
“混账,皇贵妃也是你们能编排的?还不快回去做事!”
年素鸢迷迷糊糊的,只能隐约听见如玉的呵斥声。她有些想笑,忽然觉得不对。
嗳,她不是刚刚才把钮钴禄氏的尸首送走么?怎么现在好像是躺在床上?
她努力想睁眼,眼皮却沉甸甸的,仿佛灌了铅。
“主子可是醒了?”耳边有人低唤。